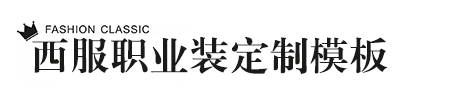民国和抗战时期普通人家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
父亲于2015年过世,在2008年他身体尚可的时候,在电脑上留下了十几页的回忆录,记录了他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今年元月,母亲也过世了,整理家中遗物,又翻出了不少老照片和资料,整理和归纳后在网络上留下一个记录,也能让不少人了解一下那个战火纷飞年代,普通人家的生活是怎样的。
文中提到的所有人都已过世,因此记录的是真实姓名,也会附上老照片。内容文字,除了错别字进行了更正,语序,用词等均为父亲原文,不做改动,我本人做的一些备注写在括号中。
家庭背景
1934年我出身于浙江嘉善一个大户人家,父辈有兄弟姐妹五人,大伯父张锡卿,二伯父张家华,老三为我父亲张家光(我的祖父),五叔父张家辉,姑妈张蕴玉。这大家庭唯一留给我一点朦胧的记忆是有一座很大的宅子。我出身时除姑妈住在上海外,四房家庭都生活在同一幢大宅内,房子很大很深,共有几进我已毫无影像,反正每房一进,楼上楼下。南面隔条小路还有一个不小的院落,内有茂密的竹林,是我们家族的祠堂,祠堂里排列着我们祖先的牌位,家族的堂号为清华堂,因为直到解放前每年母亲都要带我们去祭祖跪拜,印象很深。祖父张少卿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在我出身前早已去世,整个大家庭由我极其能干的祖母当家。我的伯父和叔父都受私塾教育,父辈中只有我父亲接受过高等教育,姑妈在上海学医。我家那时在当地也算是书香门第,妈妈和伯母婶母也都是当地大户人家出身,我妈朱宝琴受过师范教育。我出身时大家庭已开始败落,大伯父是个纨绔子弟,赌博,吸鸦片样样都有份,再殷实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挥霍,大概就在我出身前后祖母决定分家,据说当时每家名义上分得田产100亩。那时父亲在上海一个洋行工作,母亲在家抚养我们姐弟和操持家务,生活安定,小康有余。但这种小康生活在我记事前就已经彻底结束了。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嘉善相继沦陷,从此我们家庭遭受了空前大劫难。
注:嘉善属于嘉兴市,我爷爷张家光,而我太爷爷并不叫张少卿,根据我爷爷的自传,太爷爷叫张继泉,也并不是中医,因该是地主,并无职业,这点我相信我爷爷的回忆,自己父亲总不会记错。家族在那时候应该是个大户人家,有祠堂,堂号,我爷爷张家光是祖辈中唯一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在上海念过两所大学。祖父的经历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记载。
不堪回首的童年生活
一.逃难经历
1937年上海沦陷前,父亲(张家光)与几个朋友离开上海去了重庆,当时我年仅3岁。据说我的五叔张家辉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地下抗日组织,并参与了暗杀敌伪县长沈XX的活动,于是我们大家庭就成了日寇和敌伪当局的追捕对象,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当时我母亲带着我五岁的姐张国英,我和年仅一周岁的弟弟张国豪流浪于江浙一带农村避难,我母亲还怀着我没有出世的弟弟张国杰,因为年纪实在太小,我已记不得到底走过了多少地方,只记得我的小弟是在1938年逃难到陶庄的池家浜出身的,故他的小名为阿驰。也依稀记得那年我们四房的女眷和孩子们以及重病在身的祖母聚集在西塘西街大墙门的五婶母娘家,一天晚上听到日寇的飞机轰炸声,几个孩子都躲到桌子底下。
那时我家母亲要带四个孩子,实在不堪负担,逃难离家时除了随身带些地契外,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带,逃难期间除了变卖田产,别无生活来源。我二伯父家膝下无子女,于是在几房长辈和祖母都在场的情况下将我过继给二房为子。不久祖母去世,几家又分开继续流浪逃难。我就随二伯母二伯父逃难到丁栅,在那里住了大概有半年,记得我在丁栅时还去私塾上过课,学过百家姓,三字经等东西,那时不到四岁,但在那里却留下了我永世不会磨灭的可怕回忆。离我们住处不远处有一座庙宇,我放学后经常去玩,有一天看到庙门外聚集了不少人,我也挤了进去,一看大吃一惊,二伯父被五花大绑地绑在柱子上,四周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从此以后二伯父再也没有回来,没过几天我大伯父也在丁栅被捕,在一座桥上我亲眼目睹了大伯父被日本兵押过的情境。五叔张家辉从逃难开始就没有回来过,已早就被日寇杀害,至此我们张家除我父亲去了重庆没有被杀外,其他三人无一幸免。二伯父被抓后,丁栅已不能再住,二伯母就带我去西塘居住。因二伯母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我母亲为了让我上正规学校念书,不久就来西塘接我回嘉善与姐弟们一起生活,逃难流浪生活至此终于结束。
注:家族真正的灾难来自于日寇入侵,父亲的大伯二伯均被日本人杀害,不过张家辉据我大哥回忆,应该没被杀,在他童年时见过一面,是个仙风道骨的道士,想来是逃跑了,而父亲并不知道。祖父在上海沦陷后,去了重庆,一直在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和财政部工作至抗战结束后才回家乡。
二.我的母亲
回到嘉善,满目疮痍,我家偌大的一座房子,已被日寇夷为平地,简直片瓦无存。后来听说日伪当局就用拆除我家房子的材料建造了当时嘉善最大的一座礼堂,名叫大礼堂(现一中旧址),仅留下了南边破旧的祠堂院落。我家已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我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姐弟投靠到我们大姨母家,首先要解决栖身之地。大姨母家就在中山街,大姨夫原是民国政府初期驻日本的一个外交官,早已去世,家境比较殷实富有,原来房子也很大很深,日寇入侵时已遭日机轰炸,靠马路的房子已成一片废墟,后边有一排楼房(六上六下)是我姨妈和表兄嫂以及表姐们居住的,表兄一家孩子很多,不下六个。再往后是原来的柴房灶间和二小间过去佣人住的平房,于是这里就是我们一家的栖身之地,想不到这一住就住到解放以后,直到我离家去上海都没有动过窝。
住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姐弟四人,大的才六岁多,小弟还在吃奶,我母亲把我们的外婆接来同住,帮着母亲看管孩子。家里已一贫如洗,父亲自去四川后一直杳无音信,一家六口,吃饭穿衣,担子全压在母亲身上,紧接着姐姐和我又要上学念书。除了母亲身上的几十亩田契外,别无可以变卖的财产。在驰弟断奶后,母亲把我们四个孩子交给外婆看管,就拼命出去挣些钱来养家,在家里买一部绳机踏稻草绳卖,到上海跑单帮,身上帮了十几斤米贩到上海,这是非常危险的买卖,要通过日本兵的封锁线,有些人就死在日本兵的枪下。母亲受过师范教育,能写一手较好看的字,后来有一段时间,总算在地藉管理处找到了一份文书工作,工资虽不高,但能有稳定收入补贴家用已是非常满足了。不久姐姐和我相继入学念书。当时嘉善城内有二所小学,一所在花园弄天主堂内,是教会学校,叫圣类思小学,正对校门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要求学生看到日本兵时要行鞠躬礼,我们当然不愿意去那所学校。另一所在徐家弄内叫珍珠桥小学(如今还在,叫南门街小学),我们一家姐弟都是在这所小学上的学。我入学时姐姐上二年级。
母亲为了我们一家六口不得不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家里生活清贫到外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平时母亲在外,我们就和外婆相依为命,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从不吃荤菜,一年中只有过节祭祖时才能吃到一些鱼肉,外婆带我们在前面瓦砾地里开垦小块土地,种些蔬菜,如小白菜,茄子,青菜,豇豆等,平时大部分吃的菜都是从地里摘的,我和姐稍大一点时就常到前面那条河边捞螺蛳来尝尝荤性,有一次,姐姐不慎掉入河中,河水很深,我大声呼喊救命,一个好心青年跳入河中把我姐救了上来,这一幕我至今未忘。从三四岁到七八岁的孩子都要玩耍,我家没有任何玩具,别人家孩子有的玩具我们都没有。别人家孩子过年有新衣穿,我们没有。嘉善有一种特有的米,叫冬双米,是一种经过发酵处理的陈米,出饭率很高,吃口非常粗糙,我们家长年就吃这种米,每年只有在过年时可以吃上几天白米饭。自从我离家以后无论到那里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冬双米。外婆为了节省一根火柴,每次烧饭时叫我用一根细香到马路对面一家天泽堂中药店里的香火上取火种。外婆平时除了看管我们几个孩子外,每天就是理回丝和纳鞋底,理回丝是为了加工鞋底线,我从小就学会了搓鞋底线,全家所有鞋子都是她和我母亲手工做的。一到晚上,家里一片黑暗,唯一的照明灯具是一盏火如荧火虫的油盏灯,偶而点上一次蜡烛已属奢侈,因此晚上是不可能做学校作业的,每天放学回到家里,首先我们都把作业在晚饭前做完,决不留过夜。从小学一年级起,我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年级中前三名,直到初中毕业,这是我唯一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回报。每学期终,我都会从学校领回一些奖品,如铅笔,橡皮,练习本等,已足够我一学期使用。
在小学三年级时,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这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家里根本没有能力送我去医院治病,我天天发烧,不想吃饭,只能躺在床上,学校是去不成了,后来母亲找到了父亲过去的一个朋友,在嘉善东门开私人诊所,名王蓝田,是武汉人,每周到我家来一到二次,为我免费看病,诊断结果是胸膜炎,胸腔积水。在今天来讲胸膜炎并非大病,只要连续用抗生素不用多久即可痊愈,可是在40年代初,青霉素(那时叫盘尼西林)比黄金还贵,即使极富贵人家也用不起,我家连磺胺类消炎药也买不起,那时王医生每周总要用一个大针筒刺入我的胸腔,抽出好几管黄水,实在体温太高,就打一针退热针退退烧,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后来胸腔积水总算消除了,因为没有持续用药,体温始终不退,一直在37.5~38度之间,母亲为我的病整天愁容满面,我看了心里极其难过,祗能在量体温时看到水银柱穿过37度时偷偷地把温度计甩几下,有时暗中喝口凉水使温度不再上升,以此来减轻一点母亲的忧虑。这一场病生了半年多。王蓝田医生是我的恩人,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一直没有忘记,解放后我想去找他好好酬谢,可他已离开嘉善,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大遗憾。在生病期间我仍自学课本,病一好即去学校跟班上学,并未拉下功课,期终考试依然排在前三名。
就在我一场大病后不久,祸不单行,家中又遭不幸,母亲的文书工作被他人替代,一家六口的生计又没有着落,为了生活,凭她原来初级师范的学历,就带了那时住在西塘的五婶母,一起离家去农村小学教书,当然不是正规的学校,就她们二人管一二十个学生,各种年级都有,没有工友,学校的一切事务都要她们做,实在照顾不过来,那时我姐快念五年级,我妈不得不让我姐休学一年,到乡下帮忙,记得每学期快到考试前,母亲回到家里出考试题和印考卷,于是考卷刻钢板蜡纸和油印的任务都由我来完成。一年后我姐回来继续上学,因为休学了一年,从此,我和我姐就一直在同一年级上课。二个弟弟国豪和国杰也都在同一学校上学。
为了这六口之家的吃饭穿衣,又要供四个孩子上学,我母亲肩上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可能受传统观念影响,家里再苦她宁可一个人抗着,也决不变卖家里仅有的几十亩田产,当时具体还有多少亩我也不清楚,我估计最多也不过五十来亩,一亩地每年能收多少租米?因为土地有肥有瘠,收成有好有坏,每年到收租期间,当地政府部门会张贴告示,规定了各乡各镇收租的参考值。我记得差的地块每亩不到二斗米,好的地块也不过三斗五升左右。(那时粮食都以石,斗,升来计量的,一斗米合现在15.6斤)。我估算过,以平均每亩收二斗五升米计算,全年收的佃租约1800斤米,还不够一家六口人一年的口粮。但这也确是我家在那一年代赖以生存的救命粮,有了这些粮食全家至少不致于饿死,我想这大概是我母亲不卖地的主要原因吧。
1945年八月,我刚念完小学五年级。一天,大街上挤满了人群,大家高声欢呼跳跃,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八年抗战我们胜利了!在这种气氛下我和弟弟们也随着人群满街奔跑和欢呼,连续好几天晚上,大街上都举行提灯会,其场面比庙会还要热闹。母亲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看见的笑容,似乎我们家的苦难生活快要结束了。
注:可以看出,在这期间,家庭的生活异常艰辛,一家六口人,靠祖母一个人的工作和家里留下的佃租过活,但我比较好奇,那时候的田产那么不值钱么?嘉善一直是鱼米之乡,土地丰饶,几十亩田产应该不至于生活清贫至此吧,也许父亲当时太年幼,并不太清楚家中的开支情况?祖父张家光去了四川后一直在民国政府部门任职,居然和家中没有联系,也不寄钱回家,那时候家里的清贫是真实的,在我姑妈的回忆中也是如此。不知那个时期其他人家中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

注:关于祖父的经历,写在另外两篇文章中